-
NO.4漳州前锋康复医院漳州市芗城区新浦路29
北大教授吴西愉:中国孤独症研究,未来路在何方?
吴西愉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他的团队主要采用实验和计算机模拟的方法,研究语言的生理机制、语音合成与识别、言语障碍。 每年,吴教授都会带着自己的学生来到星希望,进行学习和观摩,让他们接触、了解、关爱孤独症孩子,并将他们在课堂上习得的理论,在专业的实践环境中升华。 今天,吴教授又一次带领自己新一届的学生们来到星希望,听杜佳楣老师讲述孤独症,走进各个教室观摩学习,感受孤独症康复训练课堂。

/
/
现在的关注,是未来的希望
机缘巧合下,北大吴西愉教授与杜佳楣老师结识。
“杜老师在孤独症康复教研工作和公益推广领域,已经深耕10多年。她独创的专业康复技能,对工作的饱满热情,以及为孤独症康复付出的巨大牺牲,一直令我非常敬佩。”
吴教授说道。
“我一直致力于研究言语障碍,而杜老师在实操上有丰富的经验,于是,星希望就成了我们学生的一个学习和实践基地,也为我们的科研项目提供了很多案例。
吴教授希望学生们更多了解孤独症及其康复体系,包括MUST理论体系,作为北大中文系研究言语障碍的学生,尤其应该在这方面进行了解和学习。
“学生们对语言障碍研究,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但实操不足,所以他们非常感兴趣,特别想看看机构对孤独症孩子的专业训练是什么样的。我也想让学生们知道,社会上存在缺陷的人很多。
在星希望,北大学子们真实看到不同程度的孤独症孩子,对这个特殊群体有了新的认知,也了解了孤独症家长的艰辛。

杜佳楣老师为北大学子们科普孤独症
同学们现场听杜佳楣老师介绍了MUST理论体系,这是杜老师多年来一线教学经验的理论总结。自2015年提出以来,已经为5万多个家庭提供了培训支持,受到了家长的高度好评。
观摩康复老师们专业的实操课程,大家看到了特教老师对孩子们的热情投入,一堂课下来常常大汗淋漓,学生们的触动很大,一直感叹“老师们太不容易了”。

北大学子观摩星希望课堂
“除了培养爱心,我更希望他们将来能够进入这个领域——语言障碍,孤独症障碍——进行研究。欣慰的是,我的2个硕士研究生,已经在做了。”
吴教授说道。
“如果现在社会对孤独症的关注还不足够,那么我们希望,通过在未来社会中坚力量中间,沉下这个锚,能让孤独症群体的明天,更有希望。”

/
/
对孤独症的研究,任重道远
2018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将孤独症患病率的估计提升到了1:59,从20年前不足万分之一,到现在不足百分之一,足足上升了上百倍。我国因为没有全国性的权威普查,没有具体数据,但有专家预计,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一。
为什么孤独症发生率一直在提高?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
一、诊断标准的放宽。以前是非常典型的,才划入孤独症,现在是一个谱系。
二、更好的认知和社会支持体系,让越来越多的人去做诊断。
总之,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非常值得大量投入研究。
吴教授介绍道,我们在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的学术会议上设置了一个 special Sessions,讨论跟语言相关障碍的特殊议题,包括口吃、唇腭裂、失语症、构音障碍、各种嗓音障碍、孤独症等。
在这些语言障碍中,孤独症相对特殊,连成因都没有定论,治疗更是困难重重。
我们从孤独症的诊断标准看,它是行为学的标准。
导致外显行为的原因可能很多,而且孤独症彼此之间差异也很大。这些都加大了研究的难度。

我们对孤独症的了解很有限,很多是从表面去推内在。
比如,有些孩子,我们捏他一下,他们没有反应,于是有人就觉得他们痛觉神经不发达,感觉不到痛。
后来有研究发现,恰恰相反,有的是过分敏感。通过对他们血液中内啡肽(痛觉之后会分泌的一种物质,等同天然的镇痛剂)的检测,发现要远高于普通儿童,就是说他们的痛觉更敏感。
没反应不代表不痛,他们可能不知道要反应,或者怎么反应。这就是因为孤独孩子没有社会性,这是很可怕的。
基因方面的研究已经做了四十多年,但是目前也没有定论。比如有些孤独症存在某种突变,但是同样有这个突变的,却没有孤独症。
Science每年都会发布最值得研究的100多个科学问题,其中就有孤独症的成因。孤独症是广泛性发展障碍,成因很复杂,短期内可能推进,但不一定能有突破。

/
/
相比研究成因,社会接纳更重要
国内一些人对孤独症的误解,还是很多的。我们常常会听到:“没关系,多带孩子玩一玩就好了。”“我小时候就挺自闭的,不爱说话。”甚至“冰箱妈妈理论”还在不断传播……这个必须要呼吁一下。
孤独症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目前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治疗,但是可以通过及时和有效的干预,提升孩子的综合能力。
我们都知道,要让孤独症孩子多接触社会,但是事实上,这是非常困难的。
“我曾经在日本留学,在公众场合可以看到青春期和成年的孤独症人士,但是在国内,我很少在公众场合看到大龄的孤独症人士。
“孤独症家长带着孩子出门,压力很大。小孩如果做了不好的行为,大众可能还可以包容,但是如果已经很大了,再做一些不合适的事情,社会是不允许的。
“社会对孤独症,是害怕的。
“所以,首先我们应该做的,或许是帮助社会对孤独症'脱敏'。”
吴教授介绍道。
“在日本,医生会建议孤独症孩子去普通学校,对这个孩子本身的帮助或许有限,但更大的意义在于让社会知道,有这样的群体存在。
“社会是一个整体,不能说不知道、看不见,就假装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跟日本朋友谈起孤独症,他们会觉得很正常,因为他们上小学时候班上就有。
“所以,我们也应该让孤独症孩子,更多被看见。当大家都知道了,就会减少恐惧,也更容易接纳。这是一个社会应该做的事情。”
社会进入了陌生社会,不再是熟人社会;在陌生社会中,对别人的心智解读能力要更强,才能在其中谋生。
一方面我们接触人的机会减少了,另一方面对人的心智解读能力又要求很高,因此孤独症孩子在现代社会,显得更格格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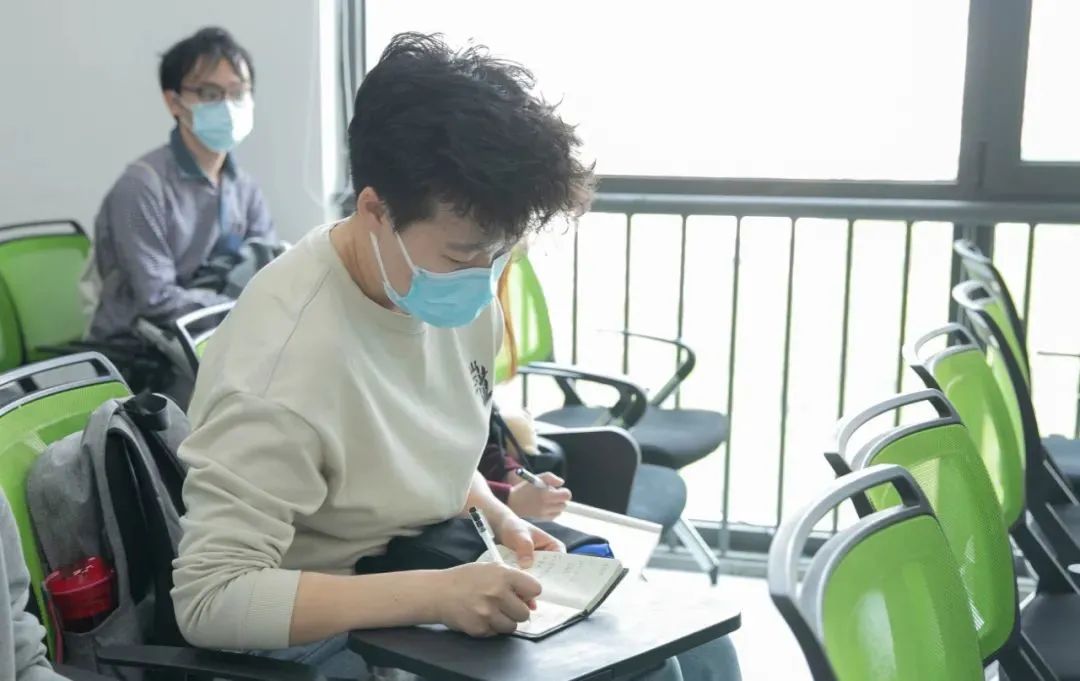
历届北大学子到访星希望观摩学习
/
/
呼吁更多公权机关的支持
事实上,在星希望或者其他训练机构,我们看到的孤独症儿童还是家庭条件不错的,很多经济能力不太好的家庭在机构里根本看不到。
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中国的孤独症患者很可能已超1000万。这1000多万个家庭,父母面临着孩子上学、就业、融入社会,以及他们离世后,孩子如何生存等一系列问题。
目前,特校或者培智学校,招孤独症的名额很少,公立的教育很不够。他们进普校也很难。即便具备了能力,不扰乱秩序,但也可能像杜老师说的,老师不敢管。“我走了,孩子怎么办?”这几乎是所有孤独症父母面临的现实焦虑。
一些家长,试图在山里建立一个介护机构,让孩子进行一些农耕活动。家长希望,在他们走了之后,孩子有一个可以生存的场地。
2017年10月1日实施的《民法总则》第一次将“意定监护”的理论变成了现实。
“意定监护是区别于法定监护的一种制度,是指成年人在意识清醒的时候,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一个临终监护人(可以是亲属,也可以不是亲属),书面指定被委托者作为自己失能后的监护人,照顾自己的生活,处置自己的财产、权利等。”
这个临终监护人可以不必是直系亲属,不必是法定继承人,可以是任何人,甚至是陌生人......
目前在上海、北京、长沙、成都等地的部分公证处已经开展了意定监护。把孩子的余生交给陌生人,需要社会有值得信任的组织,能为他们守护好孩子的一生。
在此,我们也呼吁,公权机关对孤独症群体的更多支持。
-
我国孤独症康复教育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路径
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孤独症康复教育的发展历程,从20世...
-
中国ABA应用:孤独症康复教育的发展历程与未来展望
本文概述了应用行为分析(ABA)在中国孤独症康复教育...
-
使用多重范例教学教授孤独症儿童识别他人眼神与面部方位的教学研究
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发表在《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
孤独症谱系障碍:病因、诊断与研究进展
本文深入探讨了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的病因研究历史...
-
新研究揭示了2~13岁孤独症儿童皮层发育轨迹的性别差异
先前的研究已经报道了孤独症个体大脑皮层厚度的改变。...
-
研究发现:37.1%孤独症儿童到6岁不再符合孤独症诊断标准
近日,由波士顿儿童医院Elizabeth Harstad领衔的研究...
-
孤独症幼儿测试行为特点研究
摘要:目的 探讨孤独症幼儿在发育诊断测验过程中的行...
-
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评估工具的研究进展
目的本文主要回顾了国内外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常用的评...
-
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流行病学研究:患病率、诊断与性别差异
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是一种发展障碍,其流行病学研...
-
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早期发现的研究进展
摘要:孤独症谱系障碍(ASDs)是由多种不同原因(异质性)...
-
孤独症谱系障碍:认知与社交技能的探索
本文深入探讨了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的认知和社交技...
-
自闭症/孤独症相关最新研究进展 (2024年5月)
2024-05-17报道,南方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侯圣陶...
-
孤独症康复专家吴亮:来自星星的孩子需要我们温柔地坚守
吴亮是西安交通大学儿童保健专业医学硕士,康复医学主...
-
中国孤独症行业蓝皮书Ⅳ发布会暨中国孤独症教育康复40年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2022年4月2日,是第十五个“世界孤独症关爱日”,也是...
-
孙梦麟:中国孤独症康复的探路者
从家庭主妇到行业专家,从义工体验到人生追求,从两间...
-
孤独症高峰论坛曾凡林教授分享:关于孤独症孩子的融合教育
星星桥2022国际孤独症高峰论坛特邀专家曾凡林主任谈孤...
-
孙梦麟:中国孤独症康复的探路者
从家庭主妇到行业专家,从义工体验到人生追求,从两间...
-
离开康复机构,孤独症儿童的人生何处安放
随着中国早期诊断的孤独症谱系儿童陆续长大,新的问题...
-
孤独症治疗专家贾美香:康复是长期的,家庭和社会支持缺一不可
3月的最后几天,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下称北大六院)的...
-
一个都不能少!“点亮星空 融爱未来” 关爱孤独症大型公益活动启动
1月10日讯 自闭症儿童,又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
-
世界孤独症关爱日将至 广州多名孤独症儿童体验融入幼儿园
在活动现场,孤独症儿童和健全儿童一起表演绘本剧...
-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赴南皮县开展定点帮扶工作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认真履行中央单位定点...
-
协和尤欣:潜心研究孤独症与肠道菌群之间的“秘密”
央视网消息:“彤彤快到6岁的时候,孤独症(又称自闭...
-
好消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贾美香教授答疑解惑来了!
为了帮助孤独症家长在孩子干预过程中获得更有效的教育...





















